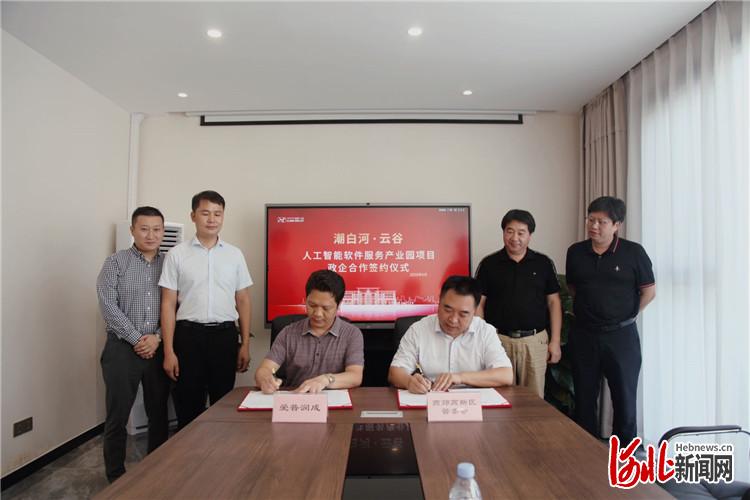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用来鉴赏艺术?
- 资讯
- 2020-12-18
- 22269

如今,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从分析数据到下棋、写诗、担任客服……在人类认为人工智能难以成功的围棋领域,4年前,AlphaGo打败了韩国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那么,再深入一些呢?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具备一定“审美”鉴别能力,在艺术鉴赏方面有所建树?
独立艺术史学者杨崇和试图在中国山水画鉴赏中引入人工智能程序。中国山水画一直被认为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再现,其中基本没有“写实”的一面。杨崇和通过人工智能的计算,提出另一种可能。他认为,从绘画中再现自然这个角度入手,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画家一直关注的是如何再现自然景物的立体感,通过焦点透视等方法,再现出景物的三维空间感。而中国山水画中并非没有写实,只是走了另一条途径:关注山石表面纹理的写实。
12月12日,杨崇和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艺术史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做客上海图书馆,就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研究的可能性展开对谈。
范景中(左二)、白谦慎(左三)、杨崇和(右一)展开对谈
西方绘画描摹现实,中国绘画描摹纹理
在艺术收藏家之外,杨崇和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芯片公司澜起科技CEO,是一个十足的“理工男”。在研究艺术的过程中,以理工科的思维,他想到了借助人工智能。
杨崇和对比了康熙时期的两幅版画。其一是1712年,康熙皇帝命画家沈喻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中的一幅,由朱圭等镂木制版,为新出版的《御制避暑山庄诗》配图。其二是康熙命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制作的相同题材的铜版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第一套铜版画。
在由中国艺术家制作的木版画中,山石上版画刻痕均匀分布,展现出山石表面受到风化和侵蚀留下的痕迹,而在意大利画家制作的铜版画中,山石上的刻痕主要是为了显示阴影,受光的石面上基本留白,没有刻痕,以此来凸显岩石的立体感。
由此,杨崇和引出了自己的假设: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画家关注如何再现自然景物的立体感,中国画家则是关注山石表面的纹理,将看到的自然纹理呈现在画作中。山水画中的皴法、点苔等就是再现的手法。
通过对10-17世纪(北宋至清初)画作的研究分析,杨崇和提出:“中国山水画风表面上不论如何改变,始终有一股源头活水贯穿其中,那就是对山水纹理再现的追求。”
“早期山水画不仅有对山石表面纹理的呈现,也有对山石立体感和山谷空间感的呈现。这种画法在宋代之后仍有使用,例如沈周的《庐山高》。但纹理再现的平面画法渐成主流。”究其原因,杨崇和认为可能是“纹理本身的二维特性更适合绘画这种平面艺术,更容易用书写的技法来呈现,因而受到文人的关注和追捧,最终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主流”。
1712年,康熙皇帝命画家沈喻绘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康熙命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制作的相同题材的铜版画
将人工智能引入艺术评论
为佐证自己的观点,杨崇和选择通过人工智能数据库来做“科学的对比”。他将古人画作与自然山水照片放入数据库对比纹理。
“山水纹理的再现技法发展至宋代已经成熟。” 杨崇和认为,宋人皴法是用笔墨描摹或模拟山石的纹理,可以看作是一种笔墨被动“拟真”自然的行为。
元人则对纹理的书写进行了“改造”,滤掉了宋画中对景物细节的繁复描绘,只画景物的关键特征。也因此,著名中国绘画史专家高居翰曾表示:“我们的确无法从宋代之后的中国画中,看到其在再现技巧上的推进或风格的转变。”西方中国艺术史学者罗樾也表示,“山水画的本质在进入元代后发生了突变,完美的再现不再是那个时代的绘画的最高追求,而一种新的表现艺术形式出现了。绘画从图绘艺术变成了一种知识型的、超越再现的艺术。(元代)与宋代相反,绘画不再是呈现客观景物的记录,而是通过风格为个人的主观感受服务。”
杨崇和则认为,在这种“超越再现”之外,从纹理描摹方面考虑,元代山水画家依然在描摹现实的尺度上稳步前进和探索。
他以传世三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笔墨与一幅照片中山坡纹理做对比。放入人工智能程序之后,台北故宫所藏黄公望真迹版描摹的纹理与现实中的山坡纹理最为接近,台北故宫所藏子明卷次之,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清初王翚按仿本的临仿再次之。
“黄公望经常去山水之中游戏观察,临写作画,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他画作中的纹理再现能力的确更高?” 从笔墨技巧而言,黄公望所绘真迹无疑艺术成就最高,结合人工智能程序的判断,杨崇和认为,纹理描摹现实的水平,可以作为艺术家艺术水平的一个判断标准。
杨崇和将三幅传世《富春山居图》中的纹理细节与真实山石纹理细节用人工智能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黄公望的真迹所绘纹理最接近真实山石细节
将日本西宫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五代时期南唐董源《寒林重汀图》中的纹理细节拿来同样做对比,更有趣的事发生了。同样是皴笔描摹纹理,黄公望所绘纹理比董源更接近真实山坡纹理图片。
“借助人工智能分析,我们发现元人虽然采用古典的皴法作画,但改进了皴法,其纹理再现的成就超越了前人。” 杨崇和认为,同样是山水画大家,元代的黄公望比前人董源纹理再现更接近真实,这是通过画法的进步实现的。
根据类似的图像分析法,杨崇和假设元末明初山水画家王蒙名作《青卞隐居图》来自于对现实中太湖石的描摹。
这也与书画评论家的见解大相径庭。《青卞隐居图》山石嶙峋,用笔快、重、急,以披麻皴、解索皴、牛毛皴为主,历来分析这幅画,都认为其绘于战乱时期,笔法表达了作者焦虑不安的心情。高居翰更是认为其中描绘与真实有很大距离:“在表达空间与形式时,不但难以理解,光线处理也极不自然。”
“如果理解为王蒙是仿照太湖石创作了这幅画,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杨崇和为自己根据人工智能对比而来的“大胆假设”找了文献证据。
根据类似的图像分析法,杨崇和假设元末明初山水画家王蒙名作《青卞隐居图》来自于对现实中太湖石的描摹。
明代书画家米万钟在其画作《天趣流鬯图》题跋中写道:“余性固爱石,偶得古灵璧石,高可二尺许,峰峦变态,奇峭如镂削,而其色泽、文理又宛然皴法自备,寔古今画家心思力量所不到者。余尝凝对终日,似颇有得,因貌一二峰于素缣,稍点缀以树屋,便觉天趣流鬯,遂成生平得意画幅。”这一题跋说明,《天趣流鬯图》所绘山水,正是出自于对一块灵璧石的仿写。
引申出去,古人“小中现大”的模仿也并非孤例。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北宋宋迪如何描述自己作画过程:“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倪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
“潮湿污染的墙壁照片,有些细节真的很像中国的山水画。”杨崇和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画家借助自然景物创作山水有此先例,甚至,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也提到过,潮湿墙壁中,有风景的痕迹:“你应该看看某些潮湿污染的墙壁,或者看看色彩斑驳的石块。如果你一定要发明一些背景,就能从这些东西中看到神奇风景的形象,饰有形形色色的群山、废墟、岩石、树丛、平原、丘陵和山谷。”
到了明代中期,吴门画派运用古典的再现技巧+新发现的自然特征,创造出新的图式和画风,在纹理的归纳和整合方面开启新局面。文征明从石质山、 土质山、树干等自然纹理中概括出“共相”,由这种统一的笔墨语汇再现不同景物的纹理。
到17世纪,以董其昌为首的文人画家走上了为笔墨,而非为真山水创作的道路,他宣称“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不如画”。杨崇和认为,这“可以说是笔墨独立于山水的宣言”。
“新的再现方法总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回归上,并同时融入新发现的自然规律或特征。”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杨崇和将中国山水画中纹理再现的演进过程概括为一条规律程式:山水画之新风格=经典的再现技法+新发现的自然特征或规律。
科学手段研究艺术,有哪些不足?
大胆假设,以人工智能的科技手段“求证”,专业的艺术史学者如何看待这种艺术研究方法?
白谦慎和范景中都肯定了将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尝试。“现在提倡跨学科,大方向上这个讲座非常启发人。”白谦慎肯定目前以科学手段去研究艺术,是未来的趋势,他也认为杨崇和找到的米万钟和达·芬奇例子“很有说服力”。
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疑问。首先是关于“像与不像”,“一种像是有意识的学习造成的,比如书法里的临摹;还有一种像是有血缘关系,但并非直接‘认识’;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巧合。比如南朝墓砖中发现一块很像颜真卿的书风,有人就认为南朝就有颜真卿这种书法了,但我认为只是巧合。这种巧合在自然生活中也会遇到,有一次我散步,看到前面有个老朋友,就去打招呼,结果并不是我以为的人,只是长得很像。偶然中的像,在生活中、艺术中都是有的。”
对于杨崇和将照片中的山水与画中山水对比,白谦慎认为有巧合的可能性,“这里也有统计学方法的问题。”白谦慎认为,杨崇和先找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根据画选了南方的山,再用人工智能去算,得出结论说黄公望画得最像,涉嫌从结论出发反向推理,“人的笔墨变化十分有限,所以相像的情况还是蛮多的。如果找100个孩子去画,然后用人工智能比对,也许其中有人对比出的结果比黄公望更接近照片,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此杨崇和解释,人工智能所做的比较,并非具体的一幅画对一幅照片,而是做了一个包含几百万纹理图片的数据包,将要对比的两张图放进数据包中去计算,“并非两张图的简单对比,而是通过庞大的纹理数据,去计算其中的‘共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找100个孩子去画,其中有人比黄公望的纹理更接近真实的概率是存在的,但大数据计算更看重的是“共象”而非“巧合”。
范景中则提出,绘画需要一套“绘画语言”,这也是美术史家赖以研究绘画好坏的依据,如果不了解绘画语言,就无法讨论作品的好坏。因而,一个艺术研究者在讨论王蒙的《青卞隐居图》时,研究的是他的用笔继承自哪些艺术家,是他使用了怎样的绘画语言,而非将他的画与太湖石对比,“即使《青卞隐居图》是对着太湖石画的,但王蒙使用的绘画语言是一以贯之的,难道他每次画画都想到太湖石吗?中国古代画论,除了笔墨,讨论的都是分类,从来不提写生,至少元之前都没有提到。分类是画家如何把握区别性特征,画家画的是共性。如果我们把艺术家使用的共性语言和个例比较,会有问题,用黄公望的具体的画在现实中找对应,不是难找,应该是比较容易。”
杨崇和肯定了研究绘画语言的重要性,“宋元画家是用古典绘画语言加上一些新发现,发展出进步,必须经历对古典画法的继承,是站在巨人肩上,并不是简单的新发现就能创新。”但他认为继承的前提下,需要结合新发现,才能实现绘画的创新。至于王蒙是否画的是太湖石,他认为这是大家“如何去相信”的问题,“我们是宁愿相信他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还是相信他有本而临?王蒙没说他绘画的来源,只是我们认为哪种更合理的问题,他自己在家随便画就像太湖石,还是他照着一个石头画所以像的可能性更大?造型上,是因为要打仗了内心积郁画出这样的画,还是照着太湖石画出这样的山可能更大?这是一种分析,最终还是大家怎么去相信的问题。”
杨崇和研究画家用笔是否更接近真实,用的是照片做比对,就此,范景中还提出“照片是否更接近真实”的疑问,“镜头是根据一定程序设定运作,拍照出来的结果,和画家经过笔墨的选择绘画是一样的。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描述是有一套语言支配的,相机也是如此。”
“人看事物有投射的一套机能,这涉及到的问题太复杂了,要解决其中的问题必须要有科学家来解决。”范景中表示,用科学手段去研究艺术,的确蕴含着令人期待的前景,“杨先生是理工男,我们把这些问题摆给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用一本书给我们做出令人兴奋的解答。”
本文由woniu于2020-12-18发表在中国AI网,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www.chinaai.com/zixun/49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