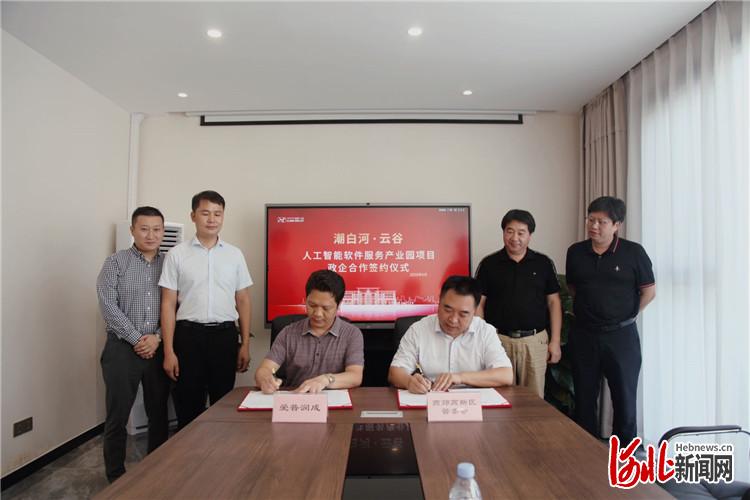狮子的尾巴有什么作用_狮子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和功能
- 百科
- 2022-09-27
- 10177
我们之所以把人体内的DNA叛逆,与由外界入侵的寄生病毒作比较,主要原因是两者实在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实际上,病毒很可能是起源于脱逃的基因的 ********* 。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别的话,那么基因有两种:一柄是透过传统的精子或卵子的途径繁殖的,另一种是透过非传统的“旁门左道”繁殖的。两类都可以是从染色体起源来的基因,也都可以包含外来的、入侵的寄生物。义许就如我们推测过的,我们应将所有自己的染色体基因,看做是相互寄生的东西。

两类基因的重要差别,在于将来它们所得以利用的环境不同。不过,引发感冒的病毒与人类染色体基因片段,彼此都希望寄主打喷嚏,好把病毒喷出体外狮子的尾巴有什么作用;传统的染色体基因及透过性交来传染的病毒,双方也都希望寄主从事性交,双方都希望寄主在性方面有吸引力。甚至,传统的染色体的基因及透过寄主的卵子传送的病毒,也都希望寄主不但在求爱上成功,在性生活上成功,甚至希望将来寄主也会是忠实的、疼爱子女的父母以至于祖父母。我想这是相当引人深思的念头。
石蚕蛾幼虫住在它自己的房子里,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到的寄生虫也都寄生在寄主体内。也就是说,基因与它们延伸的表现型之间的距离,就如一般的基因和它们的传统表现型那样近。不过基因也可隔着一段较远的距离起作用,延伸的表现型也可到达很远的地方。记得的最长距离是横跨一个湖——海狸的水坝,那就像蜘蛛的网,石蚕蛾的房子——可说是这世界上真正的奇迹。
我们不十分清楚,海狸的水坝在进化上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海狸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及精力去建造水坝,一定有它进化上的目的。海狸水坝所围出来的湖,可能可以保护住所免受猎食者的侵袭,而且也提供了便于旅行及运输木头的水道。事实上,海狸利用漂浮的道理,与加拿大的木材公司运用河流,及18世纪的煤炭商人利用运河的道理是一样的。不管好处是什么,海狸的湖是景观上一个很明显的特写。
当然,海狸的湖也是表现开明的,并不亚于其牙齿和尾巴,而且是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自然选择必须有遗传的变异才能发挥作用,在此,自然选择所选择的必定是好的湖与较差的湖。自然选择会偏爱那些“能制造利于运输树木的好湖”的基因,就如“制造利于伐木的好牙齿”的基因会受到偏爱一样。围湖是海狸的基因延伸的表现结果,可延伸好几百码之远。
寄生虫并不一定都得居住在寄主体内,它们的基因也可以相隔一段距离才在寄主身上显现。例如,小布谷鸟并不住在知更鸟或苇莺体内,也不吸它们的血或吞食它们的身体组织,不过我们毫不迟疑地将布谷鸟归类入寄生动物里。因为布谷鸟所适应出来的能操纵养父母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布谷鸟的基因从远处制造的延伸表现型。
我们很容易同情受骗帮布谷鸟孵蛋的养父母。有些从事采集鸟蛋的人,也曾经把布谷鸟蛋和云雀或苇莺的蛋(不同种的母布谷鸟所侵袭的寄主种类也不同)给弄混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当小布谷鸟几乎已长齐羽毛,快会飞时,养母仍然是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模样。此时的小布谷鸟已比“双亲”大出许多,有时甚至是大得可笑。
此刻,我们在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只已成熟的麻雀,它的体形比起它那巨大的养子是那么的娇小,逼得它必须站在养子背上才能喂饱它,在这儿我们对寄主并不觉得怎么同情,我们反而对她的愚蠢表示了不可思议。再笨的人想当然也可以看得出,那么大的小孩一定会有什么问题。
应该认为,小布谷鸟必定不只是愚弄它们的寄主,或假装成别种鸟而已,它们似乎是像毒品般影响着寄主的神经系统。这即使对于没使用过毐品的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换个例子来说,有些男人看到印有女人的图片,就会感到极度的件兴奋,狮子的尾巴有什么作用他并不是愚蠢到认为印刷的图案里有个活生生的女人,他也知道自己不过是在看纸张墨迹,但是他神经系统的反应,却有如看到了个活生生的女人。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也许会觉得某个异性的吸引力特别难以抗拒,但是仍然可以用理性来抗拒,因为自我判断告诉我们,与那个人牵扯在一起对谁都没有长期的好处。这就与抗拒食物相同。不过鸟雀就没有这种能力了,它不可能理解清楚自己长期的最佳利益是仆么,因此我们更不难理解,它的神经系统会觉得某种刺激无法抗拒。
小布谷鸟的红色大嘴巴是那么诱人,所以鸟类学家常常看见,母鸟将食物丢进别人鸟窝里的小布谷鸟嘴巴里!一只母鸟可能嘴巴里衔着给自己子女的食物,正往家的方向飞行,突然间,它从眼角看到与自己很不同种类的鸟巢里,有一只小布谷鸟正张着红色的大嘴巴,结果它转向那个鸟巢,把原木要给自己子女的食物丢到小布谷鸟的嘴里。这个“不可抗拒说”,与早期德国的鸟类学家所说养母“上瘾者”的行为类似,而小布谷鸟正是具有它们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为了公平起见,还必须附加一点说明,这种说法在最近的实验家当中不太受欢迎。当然,无疑的,如果我们假设小布谷鸟的大嘴巴,是一种如毒品般有力的超级刺激物,整个事情就容舄解释多了。而且我们也较能同情那只站在养子的背上喂食的娇小养母,她并不是被愚弄,愚弄也不是正确的字眼。她的神经系统被控制了,就如无助的毒品上瘾者那样无法抗拒。或者说,小布谷鸟就像科学家一样,已在养父母的脑部插上无数的电极棒。
现在即使我们对被操纵的养父母感到深深的同情,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自然选择让布谷鸟如此逍遥?为什么寄主的神经系统没有演化出抗拒红嘴巴毒品的能力?答案也许是自然选择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也许布谷鸟是到最近的几个世纪,才开始侵扰它们现在的寄主的,而在几个世纪后,就会被迫放弃现在的寄主,改为侵袭别的种类。
我们有一些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们总觉得事情并不是那么单纯。布谷鸟与任何一种寄主之间的“武器竞赛”,在进化上有先天的不公平性,这起因于不平等失败代价3每一只刚孵出的布谷鸟,乃是一系列的小布谷鸟祖先的后代。这些小布谷鸟的祖先,必定都曾成功地操纵过他们的养父母,而那些即或是短暂操纵失败的小布谷鸟,下场一定都是死亡3不过在养父母方面呢,它们一只只也都是一系列先祖的后代,只是这些先祖很多是从未遇到过布谷鸟的。而那些曾遭遇到布谷鸟侵入的养父母,可能在屈服于布谷鸟后仍旧幸存下来,在下一季又孵出了一窝布谷鸟。这儿的重点也就是说,失败的代价是不平等的。
抗拒被布谷鸟奴役但功败垂成的基因,可能在知更鸟或麻雀当中一代代地流传下去;而奴役养父母不成的基因,却不会在布谷鸟当中流传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先天的不公平,即失败的代价不平等。这点可用伊索寓言里的这么一句话作总结:“兔子跑得比狐狸快,因为兔子是在逃命,而狐狸只不过是在追逐一顿优美的晚餐。”我们和同事克利伯斯,将这一状况称作“生命一晚餐原则”。
基于“生命一晚餐原则”,有时候动物的行为会由于远比它们本身更重要的最高利益,而任凭别的动物去摆布。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是在为自己的最高利益着想:“生命一晚餐原则”的全部重点在于,理论上这些动物是可以抗拒接受摆布的,但是这么做却须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为了抗拒布谷鸟的摆布,也许它们需要有比较大的眼睛或者较大的脑袋,但是这些得需要一笔额外的管理费用才行。所以具有拒绝接受摆布基因的,实际上都无法成功地将基因流传下去,因为抗拒需要付出代价。
现在,我们好像又再度回到从生物个体的观点而不是从基因的观点,来认识生命了,真是这样的吗?前面我们谈到肝蛭和蜗牛的时候,已经习惯于寄生虫的基因可以影响寄主的表现型的想法,就像一般动物的基因可以影响它们自己身体的表现型一样。我们所谓“自己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加重语气的假设,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将身体内的基因,称做是身体“自己”的基因,从以上角度来看,统统都是“寄生的”基因。在我们的讨论里,布谷鸟是一种寄生在寄主体外的寄生动物,它们操纵寄主的方法和体内的寄生虫差不多,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布谷鸟对寄主的操纵和服用一般内服药或荷尔蒙一样有力,同样不可抗拒。
现在,如同表述体内寄生虫的情形一样,我们应该再将整个情形,以基因及延伸的表现型来重新表述C
在布谷鸟与寄主之间的“武器竞赛”深化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深化都是由于基因突变的发生在先,自然选择发生在后,小布谷鸟那些大的嘴巴,不管是有什么东西使它像毒品一般影响寄主的神经系统,想必是导因于基因这个突变透过对小布谷鸟嘴巴及形状的改变而生效。不过,这并不是突变最直接的效果,突变最直接的效果是对细胞内我们见不到的化学变化发生了影响,基因对于嘴巴的颜色及形状的影响其实是极其间接的。
接着就是我们阐述的重点所在了。同样的,布谷鸟的基因对被弄糊涂了的寄主行为有影响,只是更间接。我们可以说,布谷鸟的基因对嘴巴及形状是有影响(即表现型)的;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布谷鸟的基因对寄主的行为也是有影响(即延伸的表现型)的。寄生者的基因不但可以在寄主的体内,经过直接的化学方法操纵寄主,而且当寄生者和寄主分开时也可以从一段距离之外来操纵寄主。的确,化学影响也是可由体外起作用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就会看到。
布谷鸟自然是很引人瞩目的、具有教育性的动物。脊椎动物中虽然具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昆虫界差不多总有更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昆虫在自然界所占的优势是数目的众多,我们的同事梅氏(R.May)很善于观察,他说”大体上可以说,如果狮子的尾巴有什么作用你把所有物神都 ********* 在一起,你会看到几乎全是昆虫”。昆虫界里的“布谷鸟”是无法列举的,原因是数目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它们的习性也在不断地改变c接下去我们要给您看的一些例子,远远超过我们耳熟能详的布谷鸟,借助这些我们就可以实现《延伸的表现型》一书所可能激起的最狂妄的幻想了。布谷鸟产蛋以后就一走了之,但是有些像“布谷鸟”一样的雌性蚂蚁则利用一神较为戏剧性的方式,让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这是两种专门寄生在别种蚂蚁身上的寄生蚂蚁,所有的蚂蚁当中,工蚁(而不是它们的父母亲)理所当然地是负责喂小蚂蚁的,也因此,所有的布谷鸟式蚂蚁所要作弄摆布的,就是这些工蚁。
首先,第一个有效的步骤就是弄掉工蚁的母亲——女蚁王。这两种寄生蚁采取的方法是,由一个女王单枪匹马潜入另外一种蚂蚁的窝里,打出窝里的女王,骑到它的背上,然后静静地进行威尔森所巧妙叙述的死亡之舞:“它独特专长的一个动作是,慢慢地砍掉受害者的头颅。”尔后,女杀手被丧失了母亲的工蚁认养了,它们还毫不怀疑地帮,助照顾它的卵及幼蚁。这些卵及幼蚁有部分被养育成工蚁,逐渐取代了巢里原先的工蚁;另外一些变成女王的则飞到别的地方,另寻新天地及找寻头颅尚在的其他女王。
不过,砍头一事做起来有点棘手,寄生蚁如果能够协迫别人做替身,它们是不愿意劳累自己的。在威尔森的《昆虫社会》(Hie insect Societies)—书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角色是一种寄生蚂蚁。这种寄生蚂蚁经过演化的过程,已完全失去工蚁这一阶层,它们让寄主的工蚁为它们完全代劳,甚至连最可怕的工作也不例外——事实上,在人侵的寄生蚁的命令下,寄主蚁们会亲手谋杀它们的母亲!篡夺者并不需要用自己的嘴巴,它只需用些心理控制术就行了。
究竞它们是怎样控制寄主工蚁的,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谜。它很可能是利用化学物质,蚂蚁的神经系统通常对化学物质相当敏感。如果它的武器果真是化学物质,那必定不亚于任何一种桌阴险的药物。让我们想一想这种药物的作用。首先它充斥了工蚁的头脑,抓住了它的肌肉的缰绳,迷惑它,使它忘了天生的责任,然后令它违抗母亲。对蚂蚁来说,弑母是遗传上极其疯狂的行为;驱使它们做出这种行为的药物,一定是难以抵抗的。现在,读者应该知道了,当我们谈论基因的延伸表现型时,我们应该知道究竟是谁的基因会得到好处,而不是那—只动物如何使自己的基因有益。
蚂蚁受寄生蚁剥削压迫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其实不光是寄生蚁,还有其他多得惊人的各种不同的专业食客,也会剥削蚂蚁。
工蚁将四处收集来的大量食物囤积在一个地方,这就成了某些白吃食者的目标。另外,蚂蚁也是极好的保镖——不但装备好而且数目众多。前面第十章里提到的蚜虫,就是利用蜜汁来换取蚂蚁保镖服务的昆虫。有几种蝴蝶的幼虫时代,也是在蚂蚁窝里度过的,其中有一些是完完全全的掠夺者,有些则用某种东西来回报蚂蚁的保护。蝴蝶的幼虫通常以满身的硬毛装备来操纵它们的保护者。有一种蝴蝶的幼虫,头部有某种可以用来召唤蚂蚁的发声器官,在靠近尾部的地方还有一对可伸缩自如的管子,能分泌吸引蚂蚁的蜜汁;另外在肩膀还有一对能发出更为微妙的诱惑力的管口。
这些幼虫所分泌出来的东西似乎并不是食物,而是某种对蚂蚁的行为有戏剧般影响的挥发性药物。在这种药物的影响下,蚂蚁会一下子腾空跳起来,口部大张,攻击性大增,看到活动的东西比平常更加会攻击,咬、螯等。当然,非常重要的例外是绝不攻击对它下药的幼虫。此外,在“卖药”的幼虫支配下,蚂蚁最后会进入一种叫做“结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蚂蚁,变得和对它下药的幼虫难分难舍,持续上好几天之久。就这样,蝴蝶幼虫像蚜虫一样也雇用蚂蚁当贴身保镖,只不过是更技高一筹。蚜虫所依赖的是蚂蚁对掠食者正常的攻击性;而蝴蝶幼虫则为蚂蚁注射了引发攻击性的药物,同时似乎加入了某种使蚂蚁上瘾、难以割舍的东西。
我们挑选的例子都是很极端的。在自然界里到处充满着能操纵同种或异种的动植物,+过并非那么极端就是在所有受到自然选择偏爱的操纵基因案例里,我们可以正当地将那些操纵的基因,看成对被操纵者的身体有延伸的表现型作用。基因本身的位置在哪一个身体上,并不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操纵的目标可以是它所在的身体,也可以是另外一个身体!
自然选择偏爱那些能操纵世界以确保本身繁衍的基因。这一点导向我们所谓的延伸表现型的中心法则:动g的行为倾向
义们i人为i一‘心?i则易“行4,未于颜色、大小、开关及其他任何静态的表现型上。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即“生物个体和基因,谁是自然选择中的主角”的紧张局面。在刚开始的几章里,我们假设应该没有这类问题,因为生物个体的生殖就等于基因的生存。当时假设我们可以这么说:“生物为了繁殖所有的基因而努力”,或者“基因使一代代的生物去繁殖它们”。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是有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不管你选哪一个说法,只是个人的偏好而已。不过紧张的局面好像还是存在的。
弄清这件事情的方法之一,是采用“复制者”及“工具”两个专用概念。复制者也就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生存与否的基本东西,是形成一系列相㈣版本但偶尔会产生突变的东西。DNA分子就是复制者c复制者通常为了某种我们稍后要讨论的原因而聚集在一起,成为大型的共同生存机器或工具。
我们最熟悉的工具,就是身体,也就是说,身体只是工具而不是复制者。由于这一点经常被人们误解,因此我们必须稍微强调一下。工具一般不会自行地复制工具,为了繁衍它们的复制者而努力。复制者会采取行动,但不会理解这个世界,也不会抓东西吃或者逃命,它们会的只是怎样使工具做那些事情。为了多方面的目的,生物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工具的层次较为方便;不过有时为了其他目的,生物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复制者会更方便。
在达尔文的理论里,基因和生物个体并不是争夺同一主要角色的对手。相反,它们被分派的是不同的、互补的,而且在很多方面看来,是同样重要的角色!
复制者和工具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用的,特别是这两个概念澄清了关于自然选择是在哪一层面运作的烦人的争议。表面上,我们将“个体选择”摆在一个呈上升状的选择层次上,使它介于第三章里所提到的“基因”选择及第七章里所批评的“群体选择”之间,可能更合乎事物的逻辑。“个体选择”差不多是介于两个极端的中间,许多生物学家及哲学家被诱入这条便捷之道,也认为这是一条捷径。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事情根本并非如此。生物个体和生物族群,都是竞争我们生存故事里的工具角色的对手,但是两者却连复制者角色候选人都不是。个体选择及群体选择之间的争论是替代T具的争论;个体选择及基因选择则不然,因为基因和生物个体是生存故事中可以互补的最理想角色——也就是复制者和工具两个角色。
生物个体及生物群体间的丄具角色之争,因为是真实的,所以也是可以解决的。结果在我们看来,是生物个体方面获得绝对的胜利。因为群体本身太过散乱了,一群鹿、一群狮子,或者一群狼都有相当程度的基本凝聚性及目的的合一性;不过比起一只狮子或狼或鹿身体内的凝聚性及目的的一致性,太显得微不足道了。上面这个事实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不过为什么事实是如此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延伸的表现型及寄牛虫的看法可以再度为我们帮忙。
前面我们看到,如果寄生者体内的基因彼此互相合作,会不利于寄主的基因(寄主基因也彼此互相合作),原因在于这两组基因离开共同工具(即寄主)的方式不同。
肝蛭之所以可以从寄主中被分辨出来,没与寄主的目的合而为一,真正原因在于肝蛭的基因与蜗牛的基因离开生物身体工具的方式不同。蜗牛基因经由蜗牛精子及卵子离开共同的工具。由于所有的蜗牛基因对每一个蜗牛精子及卵子都有相同的利害关系,而且它们都参与了同样公平的减数分裂。正由于它们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在努力,因此化身于使蜗牛的身体变成一个有凝聚性、有目的的工具。然而,肝蛭并不是采用蜗牛的减数分裂抽签方式,它们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抽签方式。因此,这两种工具保持分离的状态,即蜗牛和可清楚区分的肝蛭,共同生活在蜗牛体内。假如肝蛭的基因也透过蜗牛的精子及卵子繁衍的话,两者可能就会演化成同一肉体,我们可能就没法区别曾经有两种工具存在了。
“单一”生物个体如我们自己,也是许多类似合并的最终具体表现。生物群体如一群鸟、一群狼,为什么没有合并成一个工具呢?正是因为它们没有离开现有工具的共同方式。当然,动物母群可能产生子群,不过母群并没有将基因以同样的容器平均传给各子群,所以一群狼的基因并不是都从未来得到好处的。但是,基因却可以借助偏护所在狼的身体,牺牲其他的狼而保障自己的福利。因此,一只狼的身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工具。
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群狼不然。从基因上来说,因为一只狼的所有的细胞(除性细胞外)都具有相同的基因,而所有的基因出现在任何一个细胞的机会是均等的,连性细胞也不例外。但是,一群狼体内的基因并不相同,同时这些细胞出现在其子群的机会也不一样。因此,一只狼的细胞和其他狼身上的细胞对抗时,所能获得的好处相当多,只是狼群之内可能有亲戚的关系,而使对抗稍微缓和一些。
一个实体若要成为有效的基因工具,必须具备以下的性质:它必须具备一条供体内所有基因通向未来的公平渠道。这对单一的狼来说是确实的,这渠道也就是那借助减数分裂形成的精子及卵子。但是这对一群狼来说就不正确了,因为基因可以自私地提升它们所在的个体的利益,并牺牲狼群体里其他基因,以此来获得好处。
你也许会怀疑,一窝蜜蜂群集的时候,似乎也同狼群一样;不过如果更详细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对蜜蜂基因来说,它们的命运大体是共享的。同群蜜蜂的基因的未来,绝大部分是决定于女王的蜂巢,这就是为什么蜜蜂群看起来,表现得像单一完全整合的工具。其实前面章节里已提过同样的看法,只是在这里说法不同而已。
我们到哪儿都会发现,生命事实上都群聚在明确的、有个别目的的工具里面,如狼及蜂窝,不过“延伸的表现型”学说教导过我们,事情不一定都是如此。
基本上,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理论园地,看成是一堆复制者的战场——它们为了在基因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而互相推挤作战。它们所用的武器是表现瑠的影响力,初期时是对细胞的直接化学作用,随后是对羽毛、牙齿甚至更遥远的东西的作用。刚好这些表现型作用大部分都无可否认地整合成明确的工具,各自的基因都在共同的精子或卵子的“瓶颈”内受到训练,并顸备被送入未来。不过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是该令人质疑的事。
为什么基因聚集成一个个的大工具,且各自具备单一的基因通道呢?为什么基因选择 ********* 在一起,共同形成可以居住的大身体呢?在《延伸的表现型》一书里,我们尝试给这些难题寻找答案。现在只能稍微勾勒出一部分答案。
我们将问题一分为三:
为什么基因在细胞里集结成群?为什么细胞会在多细胞身体内集结成群?还有,为什么身体采用称为“瓶颈”的生活史过程?
首先,为什么基因在细胞里集群呢?为什么那些古老的复制者放弃了原始营养汤时代那种自由骑士式的生活方式,而聚集成庞大的部落呢?它们为什么要相互合作?
我们从现今的DNA分子在活细胞的化学工厂里的合作情形,可以看到部分的答案。DNA制造蛋白质,蛋白质则是具备催化某些特殊化学作用的催化剂。
通常单一的化学反应并不足以合成有用的产品;在人类身体的制药工厂里,生产一项必需的化学物质需要一整条生产线。最初的化学物质不能直接转化成我们想要的最后产品,必须有一连串依照严格的程序合成的中间产品。化学研究人员的大部分智慧,都集屮在找出从开端的化学物质到期望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可能有的中间产物及可能发生的流程c同样的,一个有生命的细胞里的单一催化剂,通常也无法独立将某一个化学原料合成为有用的产品,这中间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催化剂才行。换句话说,由其中的某一个负责将原料催化成第一中间产物,另外一个将第一个中间产物转变成第二个中间产物,依此类推。
生物体内有整个生产线所需要的催化剂,它们的每一个都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基因所制造的。如果说某一个合成过程需要一系列的六个催化剂,那么制造这六个催化剂的六个以上的基因必须都有,缺一不可。做成同样产品的流程很可能有二条,每条都需要六个不同的催化剂,而且除了这两者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化学工厂里这样的情形是有的,究竟哪一条被采用,可能是历史的巧合,也可能是化学家有些刻意计划出来的。
在自然界的化学反应里,选择当然绝不可能是刻意的;它们都是经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不过,自然选择又如何使两条化学反应流程不发生混合,又如何使彼此适合的基因组合出现呢?这和在第五章里所提出的英国及德国划船选手的类比,道理是很相似的。重要的是,在流程I的某一阶段的某一基因,在同一流程其他阶段的基因存在时也能活跃,但在流程II的基因存在时却不然。如果大多数生物族群属于流程I的基因,自然选择就会偏向流程I的其他基因,流程II的基因便要遭不利,反之亦然。
流程I的六个酵素的基因被一块选上了,这种说法虽然很诱人,但却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每一个基因都是以“一个独立而自私的基因”单位而被挑选上,但是只有在适当的基因组合下才会茁壮成长。
今天,基因的合作完全是在细胞内进行的,这种合作肯定来源于原始营养汤(或任何可能存在的远古媒体)内的自我复制分子,彼此间的初步协力合作。细胞膜的产生,则可能是为了使有用的化学物质集结在一起,免于外流;细胞里的很多化学反应其实都是在薄膜上进行的,薄膜的功用就像输送带与试管架的综合。不过基因之间的合作并不限于细胞的生化作用。
由此导向我们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细胞会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自然界会形成笨重的“机器人”9
这是关于合作的另一个问题,不过范围从分子的世界切换成规模较大的东西。多细胞体的成长超越了微观世界,它们甚至4长成大象或余鱼,不过体形大并不一*定就是好事;绝大多数生物是细菌只有极少数的生物长成大象。这使得当开放给小型生物的生活资源都用尽时,大型生物还有很多可依赖的自下而上的资源。譬如说,大型生物可以吃小生物,也可以避免被小生物吃掉。
作为细胞俱乐部的一员,好处是不限于体形的大小。俱乐部里的细胞各有专长,每一个细胞因此能更专精于它分内的工作。专业细胞为俱乐部里的其他细胞服务,同时也受益于其他专业细胞的专长。如果细胞的数目很多,那么有些可以当做是侦测猎物的感觉器官;有些可当做是传达信息的神经;有些可当蜇刺的细胞,使猎物麻痹;另外一些成为肌肉细胞,好移动触手去抓猎物或分泌细胞以分解猎物;还有其他的可吸取猎物汗液的细胞。
我们必须记住,至少在现代生物的身体如我们自己的身体里,细胞都是无性繁殖出来的,细胞里所含的基因都是一样的。专业细胞的不同,只是所后用的基因不同而已。.
每一类型细胞里的基因,能帮助少数专门负责生殖细胞中的自己的复本.,生殖细胞就是氷不休息的种子生命线,其他类型的细胞则会保护这条生命线的延续。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身体要从事“瓶颈”的生活史?
首先,我们所说的“瓶颈”是什么意思?.一只大象的体内不管有多少细胞,这只大象的生命却是始于一个单一的细胞,也就是一个受精卵,这个受精卵便是一道狭窄的瓶颈。在大象的胚胎发育时期,这个瓶颈变宽到形成一只有数以千亿计细胞的大象。这些细胞不论数量有多少,专业的种类有几种,都一同合作,履行使一个细胞成为一只大象的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工作,而后再合力达成“生产单一细胞,精子及卵子”的最终目的。
大象不仅是以一个单细胞即受精卵开始的,也以生产细胞即下一代的受精卵为最终目的。于是,体积庞大、笨重的大象的生命始于瓶颈,也终于瓶颈。这样的瓶颈是所有多细胞动物及大多数植物的生活史特征。生物为什么要如此?其意义究竟何在?生命若不是这样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为了帮助理解和思考,让我们假设有两种海草,一种叫破瓶草,另一种叫吹牛草。吹牛草是一堆散落、没有固定枝条的海草,枝芽有时会断掉流走,这些枝芽可以是身上的任何部分,断下的枝芽也可大可小,它们就像园艺中的接木,也可长大成跟原来的吹牛草一样。断枝接木法便是这种海草的主要繁殖方式。随后你会注意到这实在跟它成长的方式没什么两样,只是生长的部分彼此分离开罢了。
破瓶草看起来很像吹牛草,也长得零零散散的,不过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破瓶草的繁殖方式是通过释放出单细胞的孢子,并任其在海中漂流,长成新的破瓶草,这些孢子不过是植物身上的细胞而S,跟其它的细胞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破瓶草也跟吹牛草的繁殖方式一样,是无性繁殖,即一棵植物的女儿所含有的细胞,跟它的母亲的细胞都是细胞植株的伙伴。
两种海草惟一的不同是,吹牛草依赖分割出一堆堆含有无数细胞的自身而繁殖;破瓶草则是分出一堆堆永远含单细胞的自身而繁殖。通过设想的两种海草,我们找到了瓶颈及非瓶颈的重要不同点了。破瓶草将自已一代代从一个单细胞的瓶颈挤出来而繁殖,吹牛草则只是生长及分裂为二,这很难说得上拥有明确的世代。破瓶草又是如何呢,下面再说。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答案的端倪了。破瓶草似乎已经具备一种比较明确的“生物的”感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吹牛草生长的方式与繁殖的方式一样,事实上它们儿乎根本就没有繁殖,破瓶草则是在生长和繁殖之间有很清楚的界线,我们或许已经找出不同的所在了,不过那又怎么样呢?它的意义在哪儿?重要性又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人们想了很久,答案是什么?发现问题比找出答案还难!答案可以分成三部分,前两部分与介于演化和胚胎发育间的关系有关。
首先,请想象一下器官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我们不必局限于植物,事实上目前的论点转移到动物可能比较好些,因为动物的器官很明显地复杂多了c另外,我们也不考虑性的问题。在这里,有性生殖对无性生殖的问题,只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可以将动物想象成是利用释出无性的孢子来繁殖的,而这些单细胞孢子在基因上不但彼此相同(除非经过突变),跟母体内的所有细胞也完全相同.
高等动物例如人类的身上的复杂器官是由较简单的原始器官渐渐演化而成的。不过,那些原始器官并不是像“铸剑为犁”一样,完全变成了后来的模样,它们+仅没有完全改变,而且现在需要强调的重点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不可能完全改变。像“铸剑为犁”般那样直接的转变是非常有限的。真正彻底的改变只能依靠“重新回到制图板”来完成,即丢弃原来的设计并重新开始。
当工程师回到制图板重新设计某一物品时,他们不一定丢弃原来的构想、设计,不过他们也不是试着完全将旧的物体转变成新的物体,旧的物体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或许你能将一把剑敲打成犁头,可是尝试把螺旋桨推进器制成喷气发动机的引擎,就根本办不到了,你必须丢弃螺旋桨推进器,重新回到制图板上。
当然,活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在制图板上设计出来的,不过活的东西倒是会回到新的始点。每个新一代都是~^个全新的开始,每一个新生物都是由一个单细胞开始,然后长成新生命的。新生命以DNA程序的方式继承了古老设计的理念,不过并没有继承祖先实际拥有的器官,它并没有继承母亲的心脏。然后重新铸成一个新的(甚至可以改良的)心脏,而是重头开始:从一个单细胞开始,一个和它母亲的心脏有同样的设计,或许也经过改良的单细胞开始,然后长出新的心脏来。
你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将要下的结论是什么了,瓶颈式生活史的重点之一是,它等于使生物的生命能够重新从制图板的阶段开始。
生活史的瓶颈有第二个相关的影响,它提供了调节胚胎发育进度的“日程表”。在瓶颈式的生活史上,每一个新的一代都经过一系列差不多一样的事件。首先以一个单细胞开始,经过细胞分裂而成长,然后经由释出子细胞而繁殖,最后大概难逃一死——不过对我们凡人来说,这倒不是那么重要,对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只要现存的生物已经繁殖,新一代的生活史已经开始,那么前一个生活史也就可以结束了。虽然理论上说来本在生长过程中随时都可以生殖,但是我们可以预料得到,最适宜生殖的时机终于会来临,太早或太晚释放出孢子的生物,会比那些养精蓄锐到最佳时候才释出大量孢子的对手,有较少的后代。
现在,我们的论证进人一般刻板的、反复的生活史思路了。每一代不仅仅是从单细胞的瓶颈出发,也有相当固定的生长期,即“幼年时代”。这样一个固定时间的刻板的生长时期,使得特定的东西能在胚胎发育时期的特定时间里成长,有如遵守一张日程表。在发育期中,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程度下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细胞分裂。这个程序在每一个生活史都会出现——每一个细胞在细胞分裂的名单上,都写有它特定的出现地点及时间。
有些细胞出现的时间地点是那么的明确,以至于胚胎学家甚至可以为它们分别命名,而且针对某一个生物的某个特定细胞发育阶段,你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生物体内,找到完全相同的对等阶段。
刻板的生长周期因此等于提供了一个时钟或日程表,借助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各种事件,按时启动。想想人类本身,是多么自然地利用地球每天的自转及每年绕着太阳的公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样地,瓶颈式生活史所强加的千篇一律的生长周期,也会被用来安排胚胎的成长,这看起来几乎是尤可避免的。由于“瓶颈一生长周期”的日程表确有所谓的特定时间,因此特定的基因可以在特定的时间被打开或关掉。如此精确调节的基因活动,楚胚胎演化至能够雕琢复杂的组织及器官的先,决条件,这例子太多了。老鹰的眼睛或燕子翅膀的精确性及复杂性,如果没有精准的规则来控制,是不可能产生的。
第三个影响瓶颈式生活史的是和基因有关的,在这里,破瓶草及吹牛草又再度帮助我们。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要再次假设两种海草都属于无性生殖,设想它们可能如何演化。演化需要基因的改变,即突变,突变可发生在任何细胞分裂时。
吹牛草上每一节断下来流走的枝芽都是多细胞的,细胞血系是渐行渐宽式的,刚好和瓶颈式的相反o因此,在吹牛草新生命身上的二个细胞间的亲缘关系,很可能比其中任何一个与母体内细胞的关系还远。我所谓的“亲戚”,确实是指堂兄弟姐妹这样的称谓,再以其称呼身体内的细胞。
破瓶草与吹牛草在这一点上的差异甚大,一株第二代破瓶草体内的所有细胞,都是从单一孢子细胞来的,所以同一株破瓶草体内的所有细胞,比起不同株体内的任何细胞,都是较亲的堂兄弟姐妹或其他近亲。
有关这两种海草间的差异,基因的影响很重要,清想象一下某个新突变基因的命运。首先,是吹牛草;其次,是破瓶萆c对于吹牛草,新的突变发生于任何一个细胞茎根枝桠,吹牛草的血系由于是渐行渐宽式的,所以突变细胞的直系子孙可能同时出现在第二代身上,它们与亲本的关系较远甚至未经突变,甚至可以出现在第三代身上。另一方面,一株破瓶草体内所有细胞最近的共同祖先,年纪并不会大于提供这株海草与生命瓶颈开端的孢子,如果那个孢子含有突变的基因,那么这颗新海草的所有细胞也都含有突变的基因;如果孢子不含突变基因,那么所有的细胞也都不会存。同一株破瓶草的细胞在基因上比吹牛草更为一致。对于破瓶草,每一株草都是拥有相同基因的单位,因此可以称之为个体。吹牛草的植株基因上则较为不同,甚至会有不同时期的突变出现在同一植株上,因此比起破瓶草就称不上个体了。
这并不只是名称的问题而已,只要自然界有突变,一株吹牛草身上的细胞便不会有遗传上相同的利益,吹牛草细胞内的某一个基因,只要借助提升细胞的生殖就会获得好处,但是如果它提升的是一株植株的生殖力,就并不一定获得好处,因为在渐行渐宽式的生殖情况下便会使一株棺物里的不同细胞在遗传上不一致,因此细胞与细胞在制造器官的新植株时,就不会心甘情愿地合作。如此自然选择便会在细胞间节选,而不是在植株间选了。
另一方面,一株破瓶草的所有细胞很可能都有一样的基因,只有极新近的突变才可能将它们区分,因此同一株破瓶草内的细胞都很乐意合作,以制造高效率的求生机器,不同破瓶草植株身上的细胞,可能有不同的基因。毕竟通过不同瓶颈的细胞,除了最近发生的突变外都可以辨别出来,自然选择因此检验不同的植株,而不是翻查不同的细胞(像在吹牛草那样),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益于整株植株的器官及设计的演化。
顺便)If那些有专业兴趣的人提一下,这儿还可以提出一个关于群体选择的论证类比,我们可以将生物个体看成是一群细胞,假若我们能够用某种方法,来提高生物族群内的变异对族群外变异的比率。那么我们也等于创出了某种群体选择方式,群体选择方式论就可以成立了。瓶颈式生活史与本章占有极大篇幅的另外两个想法,有相似之处,虽然这可能有些启发性,但是我们不准备去深人探讨。第一个想法是寄生虫愿意和寄主合作,其合作无间的程度可以密切到寄生虫的基因与寄主的基因都经过同样的生殖细胞繁殖到下一代,而也就是挤过了同样一道瓶颈;第二个想法是,因为减数分裂是个非常公平的方法,所以实行有性生殖的身体细胞,彼此会互相合作。
总之,我们看到为什么瓶颈式的生活史,会助长生物进化成“工具”的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可称为重回制图板、规律的时间周期以及细胞的一致性。究竟是生活史瓶颈在先还是生物个体在先呢?相信两者是一起演化的。我们猜想生物个体的主要特色,在于它是一个以单细胞作为开始和结束的单位。当生活史变成瓶颈时,有生命的物质似乎注定要被装进明确的单一生物体里,结果是愈多有生命的物质被装进求生机器里,机器里的细胞愈是会将精力集中运用于少数特殊的细胞身上——那些负责将共同基因运过瓶颈至下一代的特殊细胞。对丁•瓶颈式生活史和明确的生物个体,这两种现象是相辅相成、互相增强的,其中一个演化了就会强化另一个,就如恋爱中的一对男女,常常有掉入旋涡般的感觉。
《延伸的表现型〉一书相当厚重,我们不可能将它的论证压缩成一章,因此,不得不采取浓缩、相当直觉甚至印象派的方式将它呈现给大家。不论如何,我们希望已经成功地将书中的特色大体表达清楚了。
让我们以一个简短的宣言,来概观一下整个“自私的基因/延伸的表现型”的生命观。这是一种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法:复制者是基本的单位,是所有生命的主要动力;复制者是宇宙间任何能够制造复本的东西;复制者的起源是偶然的,它是源于一些随意碰撞的微小物体,可是复制者一经出现后,就可能无限制地自我复制。不过复制的过程并不是完美的,而且复制者也包含了一些彼此不同的变异,其中,有些已经失去了自我复制的能力,于是自身一旦消失了,整个种类也就不复存在;有一些还能复制,但复制的效率较差,另外还有一些则拥有某些伎俩,这些种类通常比它们的前辈及同辈好。也正是这些复制者的后代,后来支配了整个生物的族群。随着时间的逝去,世界就充满了最强而有力的聪明的复制者^
复制者的精巧生存方式逐渐地愈来愈多了。复制者不但借助本身所具备的特性,而且借助它们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而生存。这些影响力是相当间接的,因为+管影响力是多么曲折或间接的过程,都会反过来影响复制者拷贝自身的成败。
复制者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它所处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他复制者对当时环境的影响。如同英国及德国的划船选手,相互有益的复制者当彼此存在时,会占上风。我们的地球在生命进化的某个时候,这些相互合作的复制者的结合也幵始正式成形,于是明确的工具——细胞及后来的多细胞躯体,就被创造出来了。再后来,进化出瓶颈式生活史的工具也成功了,并逐步发展成为生物的现代工具模样。
生命物质经由自然包装形成的特殊工具,有一种极为突出又强劲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生物学家提出有关生命的问题时,几乎都是关于工具即生物个体;而且是生物个体首先进入到生物学家的意识里,复制者(现在也叫基因)只被看做是生物个体所使用的部分器械。
现在,通过“自私的基因”的观念,我们以很慎重的态度与不懈的意志力量,重新将生物学修正,并提醒自己:复制者不但是极其重要首当其冲的,在历史上也是现身说法的。
客观的进化及其方式总是提醒我们自己,回想一下,即使在今天,一个基因所有表现型的作用,也并非都集中在它所处的生物个体上。当然,不论从理论还是从事实来说,基因的确会穿透生物个体的墙壁,操纵着外界的事物——包括无生命的物体、有生命物体,甚至是很遥远地方的物体。稍微运用一下想象力,我们就可以看到基因好像坐在一只只具有延伸表现型威力的幅射网的中央。换一个方位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物体,则是位于众多聚拢的网的结点上——这些聚拢的网,是由许多生物体内’众多基因所释放的影响力交织而成的。基因影响力所能涉及的地方,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由基因为起点伸向表现型的箭头,已经从远到近重叠,把整个世界都笼罩了。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而且极为重要。这就是那些逬化的偶然之箭已经捆绑在一起,因此不能再称为偶然的事件,但是在理论上我们也没到称其为“不可避免”的地步。复制者已经不再是随意撤在海里的东西了,它们已经聚集成庞大的部落,即生物个体,表现型的影响力也不是平均地分配在世界各地,而是时常凝聚在同一生物的身体内。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人人了解的生物个体并不一定永恒存在,可是在这世界上,不管在那里,惟有一样东西肯定永恒地存在,能够使生命产生、进化,它,就是基因这个不朽的复制者!
(全书完)
本文由woniu于2022-09-27发表在中国AI网,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www.chinaai.com/baike/260407.html